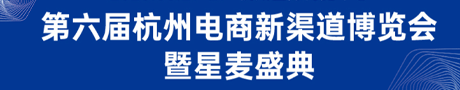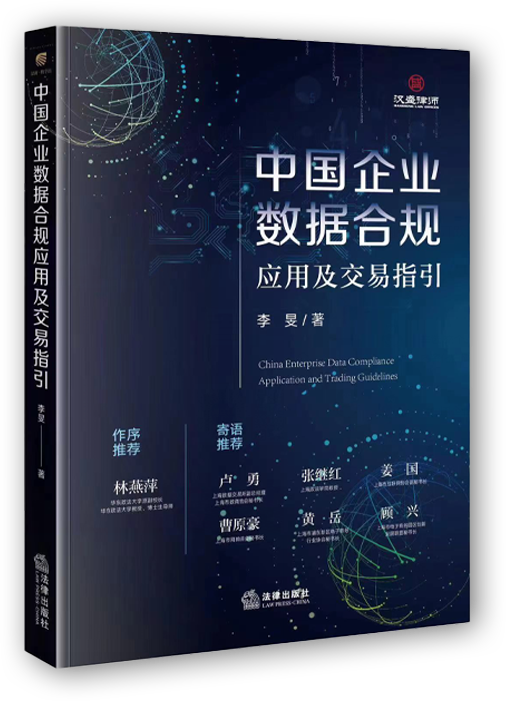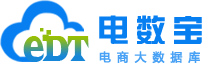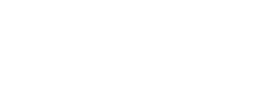(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民间俚语借助社会媒体,显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因为这些看似粗俗的表述,其流行背后,是有具体的社会现实情绪和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
从去年年中开始,“屌丝”一词在网络上迅速流行,并形成了一股“屌丝文化”。不久前,导演冯小刚发微博直斥使用“屌丝”这个词是“自贱”。上个月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屌丝”网游广告被美方停止播出。
屌丝、高富帅、白富美等词的流行,是否意味着汉语的粗俗化?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在美国广告、传媒界有规定,一些俚语以及不雅之词不允许出现。对此您怎么看?
金兼斌: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过美国传媒界是否有相应规定。但我很赞成这样的“规定”,即在面向大众的媒体上,尤其是电视、报纸上,不雅之词或能产生不雅联想的表述,通常应该慎用。
黄顺江: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等正规文化传播媒体不使用不规范用语,是对的。这是原则,应该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引导大众文化向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报》:屌丝一词的流行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心态?
金兼斌:我想更多的是一种通过自嘲来表达对自己生活现状、境况的不满意、不甘心,也可看做是对社会不公或者社会提供的个人发展环境的一种变相控诉。
黄顺江:我认为,“屌丝”一类的词语是当今我国社会矛盾状况的反映。发展很不均衡,收入差距大,社会群体产生了巨大分异。少部分人变成了“高富帅”、“白富美”一族,而大部分人则成了“穷矮丑”之类。这就是社会分层。居于下层的广大民众,内心必定会积存很多不满,发牢骚的话会经常说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阶层固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只有在市场化方面有深层次的推进,而在社会结构上却趋于凝固。例如,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放松,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农民的孩子再努力也是农民。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得到晋升,必须有强硬的后台。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经商做生意,也需要有关系。这些关系,当然也是居于社会上层的。这就使得社会上层结成了利益集团。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屌丝”之类用语的流行,反映了人们不满于现实社会,尤其是不满于自身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的无奈心态。事实上,这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通过自我矮化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其内在的心理是,一方面通过承认自己的现实窘境来自我强化必须安于现状的认知,同时又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内含着一种寻求变革的精神。
《中国科学报》: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在网络上的流行,是否说明汉语正变得越来越粗俗化?
金兼斌:应该说人们使用语言正变得越来越情景化、多样化。语言的使用场合、方式的翻新和创新,都是一种拓展,并不都是往粗俗方向演变。优雅的汉语仍然大有市场,牢牢占据着诸多重要、正式的交流场景,仍是主流,而且汉语高雅、优雅的一面,也在不断拓展。但社会媒体的发展,的确让原先缺乏显示度、只存在于市井之中的诸多俗语在社会媒体平台上大行其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黄顺江:网络文化事实上是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就不可能做到用语非常规范。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汇在网络上的流行,甚至形成热潮,基本上是大众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但这不代表主流文化的方向,不能说是汉语变得粗俗化,只能说汉语更大众化了。
《中国科学报》:上述这些词语均从经济能力、外表等方面对人进行评判,这说明了怎样的社会现状?
金兼斌:不能因为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的流行,就认为社会正变得肤浅与世俗。不同的时代,不同生活状况的人只不过有属于那个时代、环境的表达方式而已。或许我们可以说,民间俚语借助社会媒体,显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因为这些看似粗俗的表述,其流行背后,是有具体的社会现实情绪和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不完全是不着调的插科打诨。
黄顺江: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语,的确都是从经济能力和外表等方面来对人进行评判的。这些词语的流行,正说明当前社会分化严重,民众中积累的不满情绪较多。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词语的流行,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发展了,广大民众才有了发言权,并通过网络将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传播出来。这些流行词语虽然有些肤浅与世俗,但这是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进程的推进,使得广大民众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和途径。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当然,白富美、高富帅这些词汇也说明了社会上一种不健康的文化潮流。高消费,讲排场,炫耀,厌恶劳动,鄙视社会下层。这些思想意识,都是不健康的。包括“屌丝”一词,多少也有点消极的心态。所以,主流媒体应对这些思想意识进行引导。(来源:中国科学报 文/姜天海 编选:网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