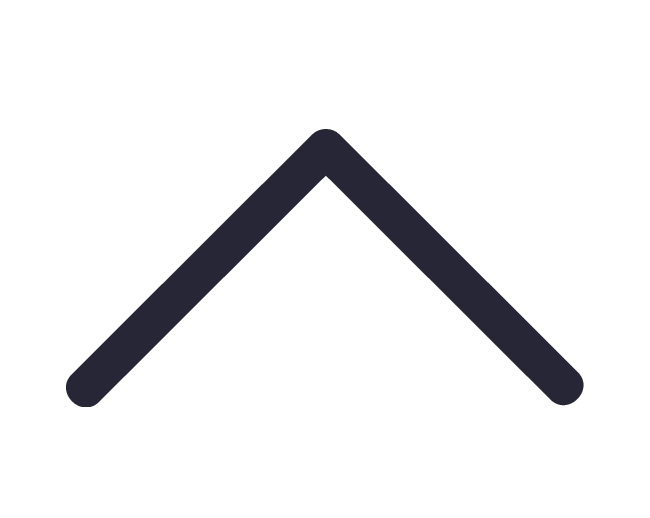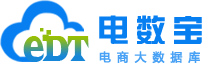(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摘要】通说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共同侵权,但其既与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不相符,又存在价值取向不均衡的正当性不足;同时,还造成了诸多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导致了实践选择与相关立法和理论的脱离。无论是从价值选择、实践操作还是从比较法经验等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都应界定为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
【关键词】网络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连带责任;共同侵权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首次从民事基本法的层面对网络环境中的侵权问题作了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条的3款规定中,第1款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加害行为侵权的自己责任,在理论和实践中未有争议;后两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需承担的连带责任,[1]该责任依据的乃是共同侵权论,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一起构成了对权利人的共同侵权,其已成为学界通说。但事实上,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很大的操作困境。本文试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以期对相关立法和司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论误区
基于私法自治,自己责任是私法中责任形态的基本原则。故除非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民事主体只应承担自己责任。详言之,主张民事主体承担自己责任的,在理论上无需加以证明;而主张民事主体承担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等其他责任形态的,则负有论证正当性的义务。其他责任形态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即体现了这一点。显然,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属特殊责任形态,且对主体利益产生了切实影响,需要给出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共同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构成共同侵权,故应承担连带责任,这是目前我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解释和论证网络服务提供者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的通行观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我国相关立法都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构成“共同侵权”来界定两者的关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2]《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表明共同侵权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
其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多遵循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是否构成共同侵权的思路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如在“中凯公司诉数联公司等著作权侵权案”中,法院认为:“网络用户在POCO网上擅自发布电影作品《杀破狼》供其他用户下载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中凯公司对该电影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数联公司尽管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教唆、帮助用户实施了上述侵权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应当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数联公司辩称其未参与也不知涉案侵权行为而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3]
其三,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两者构成共同侵权,且主要是构成帮助侵权。如有学者在解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时说:“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中,与网络用户是侵权行为实行人与帮助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实行人行为与帮助人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具言之,正是帮助人的行为,促成了实行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是基于‘帮助行为’发生的。”[4]对此规定另有学者也认为:“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却不采取必要措施,可以认定为构成帮助侵权,应当对全部损害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5]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相关立法规定、司法判决还是从学界观点来看,通说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共同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有悖于侵权法原理
尽管我国目前的通行观点是以共同侵权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连带责任,但对共同侵权自身的涵义尚存在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加害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从《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表述及第8条至第12条的体系解释来看,立法规定的共同侵权应解读为以意思联络为必要。[6]据此,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也理应符合此要件。
然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在多数情形中并不存在共谋的主观意思联络。“所谓意思上的联络是指数个行为人对加害行为存在‘必要的共谋’,如事先策划、分工等。”[7]在网络侵权中,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则两者存在共谋的主观意思联络,构成教唆侵权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主动教唆网络用户侵权的情形非常少见,相反,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在用户注册协议、内容上传告示等文件中强调用户不得实施侵权行为。从国内外受理的网络侵权案件中很少出现教唆侵权的判决可见一斑。[8]绝大多数情形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发布内容的“平台”或传输内容的“通道”,若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多依据的是构成帮助侵权。[9]然而,将此种情形认定为共同侵权中的帮助侵权并不妥当,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并不存在事先策划、分工等“共谋”行为。
以百度网站提供音乐搜索服务为例。[10]一般而言,实际侵权网站希望百度用户搜索到侵权网站中的作品链接后,点击链接能够直接跳转到该侵权网站。但百度建立深度链接的方式大大减少了百度用户浏览该实际侵权网站的几率,这显然不会是实际侵权网站所希望得到的“帮助”。对百度而言,其之所以对侵权作品建立深度链接,目的并不在于为实际侵权网站扩大侵权后果提供“帮助”,而在于吸引用户停留在自己的网站。可见,在此情形下,法律若将双方认定为存在“共谋”,将是对当事人实际意图的非真实反映。尽管法律并不要求总是“如实”反映生活事实,但原则上法律概念应尽量与生活认识保持一致,除非确有必要使法律用语偏离生活。[11]但持共同侵权(帮助侵权)论的学者或法院尚未对此种偏离的必要性做出任何论证。事实上,这一生活认识与法律解读的偏离已给实践带来了困惑。在“步升诉百度案”和“索尼等四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中,原告在诉因选择中之所以没有主张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原因之一便是担心法院对共同侵权采主观说,认为百度与被链接网站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12]
德国也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不构成共同侵权。如有德国学者认为,技术传播者,如搜索引擎,原则上不负有赔偿责任,因为其与被链接者没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结。人为传播者则原则上负有侵权责任,除非其将自己与被链接内容明确地区分开来。[13]也有学者认为,若设链者与被链接者之间存在意思联合,则被链接内容应视为设链者“自己的”内容,即适用内容提供者规则,[14]该规则下的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即自己加害行为的自己责任。
即便对共同侵权做广义理解,将主观意思联络解释为“共同过错”,而不以“共谋”为限,甚至将共同侵权解释为只需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便可构成,也仍难以证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的正当性。原因在于法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侵权提供的“平台”上的“帮助”解读为构成共同侵权与法律对其他“帮助”现象的解读存在严重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均衡。
举例而言,如果一个卖刀者在卖刀给买刀者时不知其是为了杀人,事后在买刀者杀人前,卖刀者知道了买刀者的杀人意图,但未采取措施制止买刀者的杀人行为,其是否与买刀者构成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毫无疑问,卖刀者卖刀的行为不会被法律解读成为杀人者提供了工具上的帮助,进而构成共同侵权。将此卖刀杀人事例与网络侵权加以比照可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应的是卖刀者,网络用户对应的是买刀者,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对应的是杀人行为。若依卖刀杀人事例中的侵权规则类推的话,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在知道用户侵权后及时采取措施以消减侵权后果的义务,也无需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这一类推结果与《侵权责任法》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规定大相径庭。这意味着同样是提供的工具被他人用于侵权用途,法律对卖刀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配置了很不均衡的责任。因为前者涉及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后者涉及的是受害人的著作权等财产权、人格权等。相较而言,立法采取了较轻的责任配置以避免对生命权的侵害,却采取了较重的责任配置以避免对财产权等权利的侵害。此种立法配置实难谓“罪责相适应”。对此种责任配置失衡现象,有学者试图以管领控制力的强弱来加以解释。[15]但此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控制力的强弱并不是共同(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并不会影响对它的认定。其实,美国最高法院早在1984年的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案中便已澄清,仅提供可被用于侵权用途的工具并不构成侵权,只要该工具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16]
需要强调的是,否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并不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这只能表明共同侵权不能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正当化依据。从规范性法律文件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被认定为共同侵权肇始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对之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侵权责任法》只是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却并没有将该责任的理论基础明确认定为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的这一做法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预留了解释空间。事实上,学界也已有学者开始尝试在共同侵权之外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比如间接侵权理论[17]、公共政策理论[18]、安全保障义务理论[19]等。而本文也已证明共同侵权无法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侵权责任法》的这一契机,澄清以共同侵权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传统误区,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理论基础的研究预留足够的空间,直待理论研究成熟后再予以立法上的确认。然而,最近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此却仍延续了共同侵权的思路。《征求意见稿》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定性主要体现在第6条和第7条。根据这两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主要有三:一是“共同正犯”(第6条),二是教唆侵权(第7条第1款),三是帮助侵权(第7条第1款),且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也纳入帮助侵权中(第7条第2款)。[20]《征求意见稿》实际上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作了封闭式处理,而这将限制司法实践探索的空间,也不利于促进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实践困境
立法中的制度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且当事人“愿意”依法律的规定去操作,这样的法律制度才具有正当性和效益性。若立法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操作成本过高,或当事人不会选择依法律规定的逻辑去行为,那么需要做出修正的当是立法本身。在这一前提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实践困境的关键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网络用户的追偿权难以操作,且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愿意”去操作。
第一,共同侵权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与诉讼难以操作。若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需要符合共同侵权诉讼的规则。目前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共同侵权人在诉讼中是否需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均存在很大争议。[21]如果认为共同侵权是必要共同诉讼,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实践困难在于:网络中上传侵权作品的用户可能有很多,且用户的身份信息可能并不清楚,即便查清,其所在地可能非常分散乃至在国外,故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则诉讼成本往往会非常高或根本难以操作。其实,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将共同侵权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对待时期,法院在审理网络侵权案件时也从未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来对待。这显示了共同侵权理论解释与司法实务的脱节。
第二,如果认为共同侵权人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人,那么依据共同侵权提起诉讼所存在的问题仍会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网络用户追偿时暴露出来。依共同侵权理论,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赔偿了所有损失,其有权向网络用户追偿。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这一追偿很难实现。首先,其往往面临网络用户身份不明的困难。即便查明其身份,又可能遇到网络用户分散,各自起诉成本较高的难题。即便网络服务提供者提起诉讼,还可能会面临网络用户提出的一些抗辩。比如,如果该网络用户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帮助侵权便无法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构成共同侵权的原先判决是错误的呢?同时,如何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否尽到了监护责任呢?此外,如果网络用户存在合理的抗辩事由,那么是否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承担了过多的赔偿,需要反过来起诉权利人要求返还多承担的赔偿?由此可见,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向网络用户追偿时会面临诸多现实难题。
第三,从目前网民的构成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用户的追偿也可能难以实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至2011年12月底网民总数为5.13亿,其构成状况是:10~19岁的网民占26.7%,20~29岁的网民占29.8%;学历结构是:初中占35.7%,高中占33.3%,大专占10.5%,大学本科及以上占11.9%;职业结构中,学生最多,占30.2%;收入结构中,月收入500元以下及无收入的共占25.4%,501~1000元的占12.5%,1001~2000元的占22.0%。[22]这表明我国网民的年龄、学历、收入都偏低。而根据经验可合理推测,在网络中上传侵权内容的较大一部分人是年龄偏低的年轻网民,尤其是一些对权利人利益影响较大的最新影音作品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侵权中,即便权利人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网络用户求偿胜诉,对于动辄上万的赔偿金而言,也很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第四,根据人理性自利的规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愿意”向网络用户追偿。“如果期待私人以法为武器保护自身权利并与邪恶作斗争,法必须在便宜性、实效性、经济性上对私人具有实践的魅力。”[23]即法律制度立法目的的实现需要主体的“自愿”参与,如果主体无法或不愿参与,那么该制度只会沦为一纸空文。《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立法设计是先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赔偿,[24]再赋予其向网络用户的追偿权以补偿其所受到的损失。然而,这一利益安排在实践中会因网络服务提供者“难以”且“不愿”行使追偿权而失效,进而该制度目标也就无法完全实现。造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放弃”行使追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追偿违背人理性自利的规律。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追偿很可能会对其在网络用户中的形象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后者很可能因此产生“寒蝉效应”,不再愿意在该网站轻易上传内容(即便其有权利上传)或干脆转投其他网站,这无疑会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更大的损失。诉讼操作困难、胜诉难以执行及追偿造成的形象损失和用户流失,这些实际因素的制约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使追偿权将是一个成本较高而收益较低的选择,故而在此情形下其理性的决定自然是“放弃”追偿权。这也为迄今为止我国尚未见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后向网络用户追偿的事实所证实。
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面临的上述困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与立法和理论的脱离,这一问题充分地体现在网络侵权的诉讼当中。无论是原告权利人、被告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法院,均未在诉讼中遵循连带责任的一般规律,即未将网络用户纳入侵权诉讼的考量之列。其表明实际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是被作为独立的责任对待,这从以下一些表现中得到了印证。
首先,从原告权利人的角度来看,受侵害的权利人并没有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作为侵权“共同体”来对待。在数个加害人造成同一损害的情形中,一般而言,受害人会将所有加害人,尤其是直接积极实施了侵权行为者,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为对受害人而言,无论是基于情感上的需要,还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将所有加害人列为被告,尤其是将积极实施侵权行为人列为被告应是常态。然而,在网络侵权诉讼中,积极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却往往并不在被告之列。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由于网络用户身份往往难以确定且赔偿能力较低,但另一方面可能也表明,受害人所针对的其实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而非网络用户。
其次,从被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其也未将自己的责任与网络用户的责任“捆绑”在一起。这表现在:其一,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认为自己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其在诉讼中理应请求法院将网络用户列为共同被告,但实际上未见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此主张或主张后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诉讼中提出的抗辩事由往往是自己不知道侵权存在或已经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鲜见作为“连带责任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网络用户潜在的抗辩事由主张抗辩的。对自己抗辩事由的关注和对网络用户抗辩事由的漠视反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关注的是自己的责任,而非自己与用户“共同”的责任。其三,承担了“连带责任”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从未向网络用户追偿过。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对用户的追偿成本较高而收益较低,另一方面可能也从侧面印证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将自己的责任与网络用户的责任视为“一体”。
最后,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如果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构成共同侵权,则按诉讼规则其应在诉讼中向原告询问是否要追加用户这一“共同侵权人”,但至今未见有法院在网络侵权案件审理中行使了此职权。此外,从相关判决书的内容来看,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总结案件争议焦点、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赔偿金额等问题上,也鲜见有对侵权用户的考量。如在“陈堂发诉博客公司侵犯名誉权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博客公司)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法律责任,其责任范围应结合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综合确定。”[25]该判决显示了法院在连带责任的认定及其承担问题上仅考虑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未考虑侵权用户,这实非法院审理共同侵权案件的常态。法院在诉讼中不向权利人询问是否追加侵权用户作为被告,也不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询问侵权用户的信息,判决也只是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加以分析,从不探讨侵权网络用户的责任问题,这些都表明了法院在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中仅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并没有将网络用户的责任纳人考量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网络用户追偿难以操作,那么权利人向网络用户求偿也会难以操作。相较而言,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无法追偿的风险难道不是比让权利人承担无法向网络用户求偿[26]的风险更具正当性吗?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首先,笔者并不否认网络服务提供者需承担侵权责任,而所否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其次,依民法自己责任原则,主张连带责任的负有证明正当性的论证义务,而前文已论证共同侵权无法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理由。[27]最后,民法上风险转移的正当性基础一般在于为弱势受害人提供倾向性保护。但网络侵权的多数情形并未满足受害人是弱势个体的预设。从审判实践来看,网络侵权的最主要类型是知识产权侵权,而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多数是一些有着较强实力的公司,实践中很少有个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知识产权的。个人因名誉权等人格权受侵害而提起的诉讼也并不多见。因此,权利人较强的实力降低了立法对其予以倾向性保护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与传统侵权相比,网络侵权的一个特殊性在于,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权利人,其都难以且不愿意向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主张权利。网络侵权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必然会面临实务操作上的困难,并导致实践不再遵循理论规则。立法设计和理论解释若罔顾法律对生活世界中当事人的“实然”意义,而只满足于其在条文和理论上对当事人的“应然”意义,将可能导致立法和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立法和理论改变了现实,而只会是现实脱离了立法和理论。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应承担按份责任
如前所述,为了与一般侵权理论及《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规定相符,并应对网络侵权责任认定及其承担的现实操作需要,应否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改采按份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仅需要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自己责任,其责任与网络用户的责任分离。之所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认定为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从基本原则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按份责任符合自己责任的私法原则。自己责任并非不可突破,但否定自己责任需给出充分且正当的理由。目前学界以共同侵权论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理由尚不够充分,在找到更加充分的论证理由之前,应秉持自己责任这一原则。
第二,从立法政策来看,不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连带责任这一重责。对互联网的立法政策主要有二:一是保障网络用户的充分参与;二是促进国家互联网产业的良性发展。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来看,用户主动参与内容创造是其发展趋势。[28]网站为用户的互动交流探讨、展现自我创造、关注共同话题、表达自己想法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人”要求移除指定内容的通知后,认为“通知人”并非“权利人”,或通知所指内容并未侵权,从而未移除该内容,即便法院事后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此时法律也不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所有的赔偿责任。否则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旦收到通知便不加判断地一律移除相关内容,而这将会不适当地限制网络用户的表达自由并进而影响互联网产业的良性发展。[29]正如“有的单位提出,为了防止出现纠纷,目前,只要收到权利人发出的告知侵权内容的通知,就会删除搜索结果。”“有的单位提出,目前一般不对通知进行审查,一律删除搜索结果。”[30]
第三,从实践来看,以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定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有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其一,避免了侵权诉讼中的必要共同诉讼人问题。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自己责任,便无需将难以确定身份的网络用户牵涉进诉讼中。其二,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的不一致。网络侵权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是权利人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都难以且不愿意向网络用户主张权利。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后向网络用户追偿的制度设计不具可操作性。此种立法设计无法实现制度设计之初所希望达到的利益平衡。而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为自己加害行为的责任,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责任与用户责任分离,便可避免上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问题。
第四,从一般原理来看,将其认定为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符合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理,与《侵权责任法》总则的一般性规定保持了一致。依《侵权责任法》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中的规定,数人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责任形态有两种:一是连带责任,二是按份责任。连带责任的发生情形包括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教唆侵权或帮助侵权、共同危险行为以及无意思联络但每一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在这四种情形中,前两种与网络侵权不符,上文已做详细分析。第三种情形即共同危险行为是指数人实施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但无法确定造成损害的究竟是哪个行为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并没有一同实施“危险行为”,故网络侵权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第四种以每一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为要件,显然与网络侵权不符。可见,网络侵权不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总则规定的所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相反,网络侵权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分别侵权造成同一损害承担按份责任的情形完全相符。可见,依侵权法一般原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应承担的是按份责任。
第五,从理论解释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之所以承担侵权责任是因为其违反了法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的注意义务,对应的是一种“不作为”的自己加害行为,故应承担自己责任。这也正是以共同侵权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即错误地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归咎于其为用户侵权提供了“平台”上的帮助。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原因在于其未履行“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定义务可看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与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无关,网络用户构成侵权是因为其实施了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侵权是因为其未履行“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定义务,故两者的侵权责任应是相互独立的两种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种法定义务的违反应承担的是自己加害行为的自己责任。
第六,从价值取向来看,民法在设计制度时,不同制度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应保持基本一致,不应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31]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的相似性决定了可将二者予以比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之间比较密切,因为两者都属于不作为侵权,且都违反了法定的保护性义务,只不过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发生在虚拟空间内。”[32]但立法在两者的责任配置上却完全不同。就安全保障义务人而言,其承担的是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33]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则是连带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面临的是“可能”无法追偿的风险,因为直接侵权的第三人身份一般都可以确定,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后面临的是“几乎必然”无法追偿的风险,因为用户身份往往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追偿也往往是个成本较高而收益较低的选择。当然,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但立法在责任配置上如此“厚此薄彼”无疑还需更多的论证。在得以论证之前,坚持自己责任原则应是更妥当的选择。
第七,从立法资料来看,立法者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问题上似乎也存在着矛盾与不自信。据立法资料显示,《民法(草案)·侵权责任法》一次审议稿曾规定:“权利人要求提供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注册资料,网站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该规定在二次审议稿中即被删除。[34]据学者介绍,删除该条规定是为了避免“带来侵犯网络用户隐私等风险,并可能破坏网络的匿名性”。[35]这意味着权利人没有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提供网络用户资料的权利。此处的矛盾在于:一方面,立法将“合格的通知人”视为“真实权利人”而课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移除相关内容的义务,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个通知人是否为权利人抱有怀疑而不赋予其获得网络用户资料的权利。如果立法真的确信通知人就是权利人,为何不保障权利人获知侵权网络用户身份信息的权利?如果立法不确信通知人就是权利人,又凭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负有移除相关内容的义务?立法在合格通知人是否就是真实权利人上的举棋不定表明,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判断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让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此错误判断承担自己责任,而不是承担连带责任这一重责,更为妥当。
第八,从比较法经验来看,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大多没有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连带责任。以美国为例,其侵权领域的发展趋势是减少连带责任的适用。[36]同时,就其专门针对网络侵权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判决来看,也从未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责任认定为连带责任。美国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按侵害人格权与侵害著作权而分别对待。就侵害人格权情形而言,基于保障言论自由和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管理的考虑,只要侵权内容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创作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便无需承担责任,即便其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未移除侵权内容,亦不承担责任。[37]就侵害著作权情形而言,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以免责条款的方式保障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该法并未规定在什么条件下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责任,[38]更没有规定其承担何种责任形态。从美国相关司法判决和理论观点来看,其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依据有直接责任、促成责任[39]、替代责任以及自Grokster案之后新发展出来的引诱责任。[40]但无论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了哪种或哪几种责任,其承担的都是自己责任,而并不与网络用户构成连带责任。[41]就英国而言,英国传统立法和判例所确立的“许可理论”[42]是其用于应对网络侵权的主要依据,该理论并未论及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存在连带责任。同样,英国2010年的《数字经济法案》也未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就版权侵权成立连带责任。[43]
除美国和英国外,德国、法国也都没有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的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德国用于规范网络侵权的立法经历了多次变迁,目前主要实施的是2007年修改后的《电子媒体法》。该法第7条至第10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规定与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基本一致,采取的是免责条款而不是归责条款,即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责任的情形,而未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承担责任。[44]从德国法院的判决和学者的讨论来看,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承担责任,其主要关注于通过对链接行为的定性实现,如是否应将被链接网站的内容视为设链网站“自己”的内容而由其承担自己责任,[45]未见有对连带责任的讨论。而在法国,法院在早期只是追究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责任,而并未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纳入侵权责任的主体范围。[46]之后,法国法院通过《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47]认为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能成功对其网站上的侵权内容加以审查,则需承担独立侵权责任。[48]如2000年巴黎初审法院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判决存储服务提供者hebergeur在其用户侵害著作权时承担自己责任。[49]2004年法国通过了《数字经济信任法》,其后又通过了其他诸多立法,[50]但均未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四、结语
无论从价值原则、理论实践还是从比较法经验等来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界定为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更为合理。事实上,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已有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提出过异议。“有的部门提出,对于‘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可能使网站的责任过重。”“有的单位提出,我国没有实行网络实名制,权利人很难找到实际侵权人,本条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有违公平原则,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建议将‘连带责任’修改为‘按照过错大小承担按份责任’。”[51]遗憾的是,立法最终并未采纳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按份责任的意见。
尽管就应然选择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间应承担的是按份责任,但在尊重我国目前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赔偿金作出适当限制,以避免其承担过重的全额赔偿责任。从立法目的来看,要求未直接从事侵权行为,而只是提供了平台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其主要的立法意图在于通过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促进其在知道侵权内容后及时采取移除措施,以避免侵权后果的扩大,而非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权利人的所有损失“买单”。因此,只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所课以的赔偿金超过其因该侵权行为而所得的收益,便足以促进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移除措施。据此笔者建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金,以其因该侵权行为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为主要计算标准,同时考虑其主观过错的严重程度,而并非以权利人所受损害为主要计算标准。其实,司法实践中早已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赔偿金作出了限制,较低的赔偿金使其在“连带责任”之名下承担着“按份责任”之实。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解答意见》第33条至第35条也对“在网络环境中侵犯文字、美术、摄影、影视、音乐等作品著作权的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哪些因素”作出了尝试性规定。但遗憾的是《征求意见稿》对此未给出任何指导意见。因此,我们应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梳理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赔偿金的各种因素,以便于进一步规范各地各不相同的赔偿金计算标准。(作者:徐伟;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注释】
[1]为行文方便,本文以“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指代“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服务实施的侵权行为需承担的连带责任”。
[2]该司法解释于2000年11月通过,2003年12月第一次修正,2006年11月第二次修正,但本条规定的内容未做过任何修改。
[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于2008年被评为“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0年典型案例”之一,可见该判决为法院广为认可与采纳。
[4]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5]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6]此种解读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8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梁慧星:《中国侵权责任法解说》,《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
[7]同上注,张新宝书,第49页;另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7页。
[8]在美国直到2005年的Grokster案联邦最高法院才发展出了“引诱侵权责任”(inducement liability)。See 125 S. Ct. 2764(2005).美国的引诱侵权类似于我国的教唆侵权。我国司法实践中也鲜见有关教唆侵权的判决。
[9]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书。
[10]实践中此类纠纷已多次发生,例如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公司音乐搜索服务著作权侵权案(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7965、7978、8474、8478、8488、8995、10170号民事判决书)、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公司音乐搜索服务著作权侵权案(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02621~02631号民事判决书)等。
[11]此观点详见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51页。
[12]参见王迁:《论版权间接侵权及其规则的法定化》,《法学》2005年第12期。
[13]See Oliver Koster, Uwe Jurgens, Liability for Links in Germany: Liability of Information Location Tools Under German Law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E-Commerce, Verlag Hans-Bredow-Institut, 2003, pp. 9-10.
[14]See Thomas Hoeren, Liability for Online Services in Germany, 10 German Law Journal 5, 2009, P. 569.
[15]参见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6]See 464 U. S. 442(1984).
[17]这方面的典型著作可参见王迁:《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理解与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参见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
[20]参见news.xinmin.en/domestic/gnkb/2012/04/23/14514652.htm1,2012年4月24日访问。
[21]同前注[6],奚晓明主编书,第73~75页。
[22]参见 //www. cnnic. net. cn/dtygg/dtgg/201201/t20120116-23667. html, 2012年4月6日访问。
[23][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李薇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
[24]尽管在制度上权利人可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一同起诉或只起诉网络用户,但鲜有权利人会如此选择。
[25]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6)鼓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
[26]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比较的是权利人“向网络用户”求偿的风险,而不是权利人求偿的风险。即权利人承担无法向网络用户求偿的风险并不意味着权利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因为笔者赞同权利人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求偿,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独立于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
[27]下文将说明其他一些导致连带责任的情形,如共同危险等,也都无法作为论证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理由。
[28]这集中体现在互联网从Web 1.0向Web 2.0的变化。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在Web 1.0时期,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网站,用户则被动地接受其提供的信息,典型者如早期的各类门户网站。在Web2.0时期则注重用户相互间的交流,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网站其他用户创造的内容的接受者,典型者如博客网站、社交网站、微博及维基百科等。
[29]据美国的一项针对《数字千年版权法》中通知移除制度(notice and takedown)的调查显示,有31%的被移除内容存在合理使用等抗辩事由的可能。See Jennifer M. Urban&Laura Quilter, Efficient Process or“Chilling Effects”? Takedown Notices Under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22 Santa Clara Computer&High Tech L. J.667(2006).
[3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页。
[31]参见王铁:《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2]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33]“只有当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时,第二顺位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才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34]同前注[3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书,第3~4页、第11页。
[35]同前注[6],奚晓明主编书,第263页。
[36]关于美国侵权法上连带责任适用范围的近代扩张与现代萎缩,参见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6页。
[37]美国这方面的立法集中体现于1996年的《正当通信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典型案例为1998年的Blumenthalv. Drudge and AOL名誉侵权案。See 992 F. Supp. 44, 24(D.D.C. 1998).
[38]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所规定的“避风港”规则只是给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最低限度的免责保障,保证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必然不会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符合这些免责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便必然会承担责任。该法明确规定:“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未满足本条规定的责任限制条件的,不应据此对服务提供者抗辩事由做出相反的认定,即否认服务提供者根据本目(title)或其他规定所享有的不构成侵权的抗辩事由。”See 17 U.S.C.§512(1).
[39]国内一般将“contributory liability”翻译为“帮助责任”或“帮助侵权”,但这一译法易于引起误解,因为美国法中的“contributory liabil-ity”与我国法中的帮助侵权(责任)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
[40]See 125 S. Ct. 2764(2005).
[41]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自己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也是国内知识产权界部分学者主张引进美国间接侵权理论(secondary infringe-ment)的理由之一。
[42]相关立法如英国1911年版权法和1956年版权法,典型案例为Falcon v. Famous Players Film Co. [1926] 2 KB 474.
[43]该法案的两大目标之一便是试图解决网络版权侵权问题。该法案为解决网络版权侵权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诸多义务(如第3条、第4条等),这些义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和权利人找到和记录侵权用户。对于未履行规定义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该法案第14条规定可由政府部门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处以罚金,但未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用户的行为承担责任。
[44]德国的立法变迁过程及立法的主要内容可参见前注[14],Thomas Hoeren文,第561~568页。
[45]观点不同的判决如LG Hamburg, MMR 2007, 450; OLG Schleswig, K&R 2001, 220; LG Braunschweig, CR 2001, 47.
[46]相关案例如Art Music v. ENST, TGI Paris, Aug. 14, 1996; Queneau v. Leroy, TGI Paris, May 5, 1997, J. C. P. 1997, II; SNC PrismaPress v. Vidal, TGI Paris, Feb. 13, 2001.
[47]See Xavier Amadei, Standards of Liability f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SpecificFocus on Copyright, Defamation, and Illicit Content, 35 Cornell Int’l L. J.203(2001 -2002).而法国法院若判决连带责任一般是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
[48]相关案例如Lefebure v. Lacambre, TGI Paris, June 9, 1998; Lacoste v. Societe Multimania, TGI Nanterre, Dec. 8, 1999.
[49]Cons. P. v. Monsieur G.,TGI Paris, Mar. 24, 2000.
[50]例如法国《邮政服务与电子通信法典》(code des postes et des communications electroniques)、《信息社会作者权及相关权利法》(loi surle droit d’auteur et les droits voisins dans la societe de l’information)、《在网络上深化传播和保护创作法》(loi favorisant ls diffusion et ls protection dels creation sur Internet)。
[51]同前注[3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书,第69页、第608页。
原文出处:《法学》2012第5期